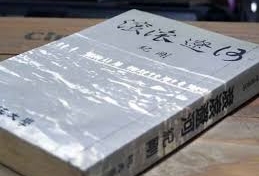Category: Other
Save Janet 一位孩童健康成長的守護者
Dear Committee members, I am writing to share a sad news with you and ask your assistance to spread the message. Janet Hsu-Lin (許捷), an emergency pediatrician, who served as […]
出走 (兩則)
木齊齊 出走 那時候年輕得像無拘無束的蒲公英, 揹著嬉皮袋隨著午后和風四處飄蕩. 嬉皮袋內常常是兩根香蕉和一把花生糖, 袋外則總是一襲紅色小風衣和孤獨卻不寂寞的我. 我喜歡坐在長長防波堤上看海浪衝擊堤岸, 像是觀看古戰場的攻城之戰, 驍勇的戰士前仆後繼搶攻城壘, 未爬上去就摔跌下來, 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既不畏懼也不退縮. 我也喜歡坐在木麻黃下看細心的海浪輕輕沖洗沙灘, 溫溫柔柔的抹盡沙灘所有傷痕. 有時候我也會嘲笑海浪像是最懂得作客之道的訪客, 造訪海灘時總是留下貝殼﹑海星之類的禮物後轉身就走. 我更喜歡嘲笑詩人的痴傻, 只會躲在燈紅酒綠裡感嘆﹕『把耳朵貼近貝殼, 你會聽見海洋的呼喚﹗』我卻希望能讓他們知道﹕『把耳朵貼向海洋, 你可以聽見貝殼的呢喃~』 那時候的我是一串平淡輕快跳躍的音符, 不久就被整個交響樂的澎湃洶濤淹沒~ 邂逅 […]
尋夢無痕
王世輝 作於11/04/07 27歲時來到波士頓,物換星移35年,鄉音未改鬢毛衰,他鄉似乎取代了故鄉。遙望似曾相識的明月,混淆的思緒中,已經無法分辨自己是中國人、台灣人、還是美國人。 在台灣留下許多童年的純真和歡笑,光著腳丫的足跡,踏遍窄巷中的泥濘路和鄰家屋頂上的石棉瓦。拖著兩條上上下下的鼻涕,頂著蒼蠅飛舞的癩痢頭,無憂無慮穿梭在殘破的矮屋和不知道名字的玩伴之間。入夜之後,沒有電視,更沒有電玩,但是有打不完的蚊子,和點不完的鱷魚牌蚊香。乘涼和搖扇聊天是大人們的唯一消遣,我只能在一旁揣測上海話裡的鄉愁,一輪孤獨的明月,似乎永遠是互道晚安時的見證。一壺熱茶,沖淡了國仇家恨;一紙家書,延續了兩岸情仇。學生的生活變得有節奏、有旋律、有變化、更有色彩。上課的時候想著福利社的冰棒,心不在焉的思緒中飄浮著鄰家的女孩。搭公車時目不暇給尋找道聽塗說的校花名草,擠在補習班裡尋尋覓覓萬綠叢中的一點紅。留在學校唸書是為壓馬路找正當藉口,上圖書館是為了表現自己是模範生。手中的原子筆畫不出想像中的白雪公主,制服口袋裡藏著不敢撥的電話號碼。上學是隨波逐流的例行公事,除了對考試的排斥和開夜車時驅不散瞌睡,青少年的歲月似乎是揮之不去的流水年華。喇叭褲、迷你裙、麵包鞋曾經是目光的焦點,湯姆瓊斯的嘶吼和觸電般的抽動成為時尚的代言。夜市的破舊板凳上有檳榔汁,還有脫離木屐的黑腳印。西瓜攤上有盤旋不去的眼中釘,小吃店的角落堆著同流合污的碗盤。理髮店裡蹲滿看漫畫書的蘿蔔頭,沒有警察的電影院有令人目瞪口呆的表演,擦鞋中心有穿著拖鞋的醉翁,釣蝦場裡只有辣妹沒有蝦。 鋼琴酒吧裡瀰漫著聽不懂的西洋歌曲,KTV的包廂裡擠滿黑道白道和手槍,寶斗里的公娼已經化明為暗成為個體戶,雨後春筍的摩鐵提供了內需的地下管道。小三文化有隱私權的加持和保護,小鮮肉成為女權運動的護花使者。本土歌曲中充滿對日本的往日情懷,靖國神社無情壓倒了忠烈祠的尊嚴。經濟起飛的光環只剩下記憶中的片段,四小龍的輝煌歲月成為你我說不出的痛。民主的糖衣侵蝕了年輕人不成熟的思維,啃老族的無知踐踏了父母的殷殷期盼。傳道授業解惑已經被雞腿和挑釁摧毀,生命的意義和價值只藏在豪門深宅裡面。政客的滔滔謊言是茶餘飯後的議題,媒體新聞的八卦捧紅了新新人類的無厘頭。不勞而獲和坐享其成是享受人生的新理念,拋棄傳統包袱是改革開放的進步指標。中華文化即將和核能電廠進入掩埋場,經典文學和四維八德已經是往日黃花,孔廟、故宮、中正紀念堂即將日落西山,國語文苟延殘喘成為不久將來的鄉音。忱摯的人情味成了爾虞我詐的祭品,敬老尊賢的美德成了選舉時的政治語言。謙沖的自尊被無知的自大所蒙蔽,劃地自限造成犬吠火車的井底之蛙。黑白之間存在無盡頭的可能,是非的界線是人云亦云的夢囈。 佇足在熙來攘往波士頓中國城一角,靜默觀察在大牌樓前絡繹不絕的遊客,他們把別具一格的牌坊當作活動佈景,恣意妄為妝扮自己美好的畫面。天下為公的意境不敵品頭論足的遊興,禮義廉恥的光環更不是鏡頭裡焦點的選擇,這是文化欣賞和認同的差距,也是自我 融入和被動接納的矛盾。菲力牛排館讓我想到巷口的牛肉麵攤,孤芳自賞的紅酒讓我想到香醇的金門純高,生冷無趣的三明治讓我想到香脆的燒餅油條,膾炙人口的龍蝦讓我想到炭火上的烏魚子,乏善可陳的生菜沙拉讓我想到清粥小菜,貧乏無味的蘋果橘子讓我想到蓮霧龍眼,趨之若鶩的牛肉串讓我想到大腸包小腸,味同嚼蠟的火雞讓我想到烤鴨三吃,高尚的星巴克咖啡讓我想到純樸的酸梅湯和青草茶,千篇一律的蕃茄濃湯讓我想到垂涎三尺的圍爐火鍋,雜亂無章的跳蚤市場讓我想到萬紫千紅的夜市,夜晚寂靜孤寂的人行道讓我想到無所不在的車水馬龍,摩肩接踵的玻璃帷幕讓我想到與世無爭的四合院,麥當勞俗不可耐的漢堡讓我想到街頭巷尾飄香的掛包,賞心悅目的港灣步道讓我想到淡水老街,老態龍鍾的地鐵讓我想到高鐵和捷運,平凡無奇的雜貨店讓我想到燈火通明的便利商店,美輪美奐的教堂讓我想到雕樑畫棟的廟宇。 朋友說這裡有清新的空氣,但是我聞不到熟悉的人情事故;朋友說這裡有潔淨的飲水,但是我飲不出街坊鄉里的同舟共濟;朋友說這裡有完善先進的醫療設施,但是我感受不到噓寒問暖的人性關懷;朋友說這裡地大物博,但是我感受不到血脈相連的親切;朋友說這裡有珍貴歷史文化景點,但是我感受不到家鄉一草一木的熟稔;朋友說這裡有循規蹈矩的人文素養,但是我感受不到守望相助的推心置腹;朋友說這裡是年輕人的樂園,但是我嗅到了老年人的墳場;朋友說留在這裡開創未來,但是我的未來是回歸不是開創;朋友說亦步亦趨跟隨子女的腳步,但是我要尋找父母留給我的腳步;朋友說這裡是人生的歸宿,但是我選擇了來時路。 月還是故鄉的圓,水還是故鄉的甜,人還是故鄉的親,景還是故鄉的美。 落葉歸根,尋夢無痕。
非洲驚魂之小江的故事
劉金本 這是小江的真實故事,在象牙海岸中共大使館幾位從賴比瑞亞逃出來的難民中的一位說的。 小江是福建人,據說是從匈牙利經過北非幾個國家輾轉來到賴比瑞亞的﹐很少人知道他的名字﹐大家都叫他小江﹐不過他的年齡也大概接近而立之年了。他起初在首都蒙羅維亞一家黎巴嫩人的修車場工作﹐因為經常到一家中國餐廳吃飯而認識了餐廳老闆“小錢” 夫婦。錢先生見他老實又勤奮﹐請他到餐廳來幫忙﹐而且也接他搬到家裡一起住下了。 他說大約十五六歲的時候﹐因為家裡很窮﹐一位堂叔帶他跟隨著一夥人到了匈牙利﹐在那裡打工打了七﹑八年﹐什麼粗活都幹過了﹐可是工資卻少得可憐﹐一直都還沒有還清當初出國所欠的債務。有一天朋友告訴他有一漁船公司要招募船員﹐便立刻跟朋友跑去應徵﹐想不到這個公司竟沒有很嚴格的調查身世﹐輕易的便被錄用了。原來這是一家南斯拉夫的漁船公司﹐他們在一艘兩百噸的漁船上﹐在地中海中來回不停的捕魚﹐經常一出海便是三四個禮拜才上岸﹐有時會在對岸利比亞的Tripoli港口下漁貨並買補給。漁船的工作是非常辛苦又枯燥無味的﹐成天與藍天大海為伍﹐碰到惡劣的天氣﹐還得與暴風雨拼命﹐難怪一到港口便會拼命找尋刺激﹐ 微薄的收入便又在港邊花用殆盡。 也是朋友的建議,他們又在利比亞靠岸時與船公司不告而別﹐流落北非﹐經過阿爾及利亞﹑摩絡哥﹑毛利塔尼亞﹑賽內加爾﹑幾內亞﹑獅子山等國家﹐輾轉來到賴比瑞亞﹐經過這些國家也沒有簽証﹐在邊境只要花些錢﹐總是有辦法而且很容易的蒙混過關的。如今在賴比瑞亞也沒有合法的居留﹐反正他也一點都不擔心﹐總是認為先掙些錢比較重要﹐等到真有一天被移民官發現遣送回國時﹐也絕不留戀的會回國定居的。我們相信他這十幾年來在國外顛簸﹐嘗盡流浪異鄉的辛酸﹐一定感到很累了吧﹗ 可是老天對他的磨難還沒有停止,真正的劫難還在後呢﹗ 那是在阿必尚中國駐象牙海岸大使館內前的一群難民聊天談起的故事﹐說故事的便是小江﹐他說﹕“ 今生再也不會有什麼事情叫我害怕了﹐因為我已經歷過人生最恐怖的事情。” 以下便是他所講的經歷﹕ “泰勒叛軍在ELWA(電視臺) 與政府軍對歭峙著﹐港口的強生部隊有一天突然繞過美國大使館來到了市中心的國家銀行附近﹐離總統府不到兩英里。我們的飯店就在新口街(Sinko st.) 的中段﹐離泰勒軍隊才三英里左右﹐住家就在飯店街道對面的一條巷子裡面。那時錢老闆已經離開回台灣了﹐他要我看守著住家與飯店﹐當然餐廳早已經關門歇業了。我每天躲在家裡﹐足不出戶﹐自認為家中所存的糧食足夠維持一個月以上﹐誰會知道惡夢在六月二十七日開始了﹐因為那天停水了﹐隔兩 天又停電了。” “停水停電讓街上的居民更加不安與恐慌,尤其在夜間經常可以聽到喧譁吵鬧的聲音。過了幾天﹐老百姓到處找水﹐雖然那時西非的雨季剛剛開始﹐但是雨水還不多﹐偶爾會有軍人載運的水車在街上配水﹐黑人百姓爭先恐後的搶著要。有一次我提了一個水桶也想去要水﹐可是人實在太多了﹐而且一點秩序都沒有﹐後來竟互相扭打起來了﹐士兵為了要維持秩序﹐竟當場打死了兩個人﹐一時群情激憤﹐最後演變成暴動﹐將兩個士兵活活打死﹐從此便不再有水車供水了。” “更糟糕的是叛軍開始用迫擊砲向著城裡無目標的亂轟,造成許多百姓傷亡﹐而醫院的救護車也不來搶救傷患。有一天我要到一家有水井的黑人家買水﹐過了一條街看見幾個黑人圍在排水溝取水﹐走近一看﹐原來一具屍體躺在溝內﹐擋住了昨夜小雨在溝裡的流通﹐造成一灘看起來很澄清的水﹐那些黑人竟把屍體視若無睹﹐一心只想取水﹐看到這種情景﹐心裡頭直想作嘔﹐同時想到局勢越來越緊張﹐以及最後免不了的一場決戰﹐令我感到害怕了。” “人若遇到緊張害怕的時候﹐有人作伴還好﹐偏偏那時只有我孤獨一個人住在一棟偌大的房子裡﹐隔壁鄰居都隔了一個大院子﹐平常也很少往來﹐如今更聽不到有人居住的聲息。夜間聽到的人聲﹑槍聲﹑炮聲﹐有時近有時遠。我把平時所積蓄的美金與當地幣分作幾份藏在不同的隱秘場所﹐有些還埋在院子裡的地下﹐只留一些賴幣在身邊﹐以備萬一遭搶時可以應付歹徒。” […]
雙子星(下)
胡宏 II. 台灣行 我們為了找這YP商旅找到這大樓的十四樓。 一路上,我妻很有信心地說: “別擔心,這家旅館的口碑很好,在網上的評價是四顆星。不會讓你失望的。” “我們從桃園機場坐地鐵過來,到了轉接站都沒有見到去旅社的路標。難道寫這些評分的客人沒有任何抱怨嗎?” “這一段的地鐵是上個月才通車的,大概是路標還沒有掛好。” 在電梯門打開的時候我們終於看見了YP商旅的招牌。三位青春美貌的服務小姐在電梯門口對我們異口同聲地說: “歡迎光臨!” 她們動作劃一地為我們辦簽到,又親熱地說: “不好意思,YP商旅正在做早晨的清點工作,你們二位先到餐廳享用早點,好嗎?我們一定會儘快把你們的房間打整好。” 她們說完就把我們請到一個舒適的起居室,還有個陽台可以看見台北市區。 “跟你說過吧,他們保證我們有地方可以休息;他們清點房間不會太久的。” 我四周看看,終於滿意地說: “沒錯。” 沒一會,我們鑽進了一張舒服的大床。正昏昏欲睡之際,我聽到妻突然說: “秀麗在外面敲門!” 我花了幾秒鐘才清醒過來,但還搞不懂為什麼我們的首席女高音這個時候會來敲我們的門。我勉強爬起來,穿上了夏天的衣著,探頭出去一望,見妻正在跟秀麗熱烈地擁抱,還告訴秀麗和大衛倆今早我們找路的事情 …. 我急於要跟老友說話,就插嘴說: “今早?現在還是波士頓的深夜呢。” 大衛發現我穿的是夏裝,馬上大笑著過來說: “你變得真快,我們離開波士頓的時候地上還有積雪 ….” “沒錯,不過台灣已經是初夏了。你記得,二十年前你離開的時候就是這樣的天氣,是吧?” 秀麗輕笑說: “其實,最近我們每年都回來看我的爸爸媽媽 […]
懷念滾滾遼河作者 紀剛醫師
張鳳 《滾滾遼河》作者紀剛,我總喊他趙伯伯。 他是我師大實習時,台北文山同事孫寶珊老師的東北抗日生死夥伴。慈藹的孫李老師伉儷,是小学同桌孫一的爹娘。孫家從東北五二三蒙難慘烈犧牲六位親人而復流徙,避隱城郊碧潭邊,從不輕露感懷,只能讀其書,懂得他們人格高華,萌發的民族殉道精神,才更加具象化。 1994年元月,周勻之主編,將我文:文化中國和儒學的創造轉化-杜維明教授刊登在世界日報週刊首頁。素昧平生的趙伯伯即來電,自年少被其愛國血忱震撼,深為遼河父祖輩血淚填成的國仇家恨所觸動, 景慕意欲刻劃者,竟積極找上门尋來,這非比尋常之欣喜, 卻瞬息變化為冷靜的興奮。 力求屏氣凝神聽電話中美西的趙伯伯說:“妳寫人物都是名人!妳可說是張開天翼的鳳凰,正作世界性的飛翔。學府藉著妳開闢路和橋,珍藏並傳揚文物。“當時來哈佛12年,寫過由諾貝爾獎恩斯特,太太邀宴而認識的瑞士朋友趙淑俠大姊,也應我之請來哈佛贈藏賽金花手稿。 自此為方便我研究,趙伯伯接二連三來函,常以優先隔夜快遞郵件,寄來一手資料和書:《諸神退位》《原來如此》《做一個完整的人》《羅大愚先生紀念文集》《一二.三0事件始末》《山高水長》等…難得一見老舊殘破依然珍存的《五二三蒙難二十週年紀念文集》和各影本偶會重覆。他常說高興尋到了我,並知賞如伯樂,互許伯樂, 把我當作實力派千里馬,也中介給《未央歌》的鹿橋教授,長輩名家前後主動到哈佛來相見,牽出輕舟擺渡致送手稿墨寶之佳話:燕京圖書館和柏克萊加大周欣平館長的緣份。 伯伯是四大抗戰小說的作者,堪稱與鹿橋,潘人木,王藍~或徐速諸家一齊聞世。 紀剛名趙岳山,1920年生於遼陽農家,滿族,在邊外開荒,幼讀私塾,中學在教會瀋陽文會書院,滿洲國治下的盛京醫科大學~遼寧醫學院畢業。 參與現地抗日地下工作,組織覺覺團。後擔任海軍醫院軍醫。渡海來臺,曾任臺南第四總醫院小兒科主任,後自開兒童專科醫院,執業廿餘年。退休為太太氣喘旅居美西。 寫書前,他脫敵偽死獄,淚別白山黑水,匆度黃河長江,56年以愛為主軸誕生十萬字《愚狂曲》,退役開業,兒科業務蒸蒸日上。每晚9點上樓直寫到夜半。病歷與稿紙齊飛,連續三年,一揮而就45萬字小說,在心中醞釀了23年故事,終於噴湧而出。先沿著看稿線,寄5位至友審閱,依次張一正、李春陽、吳尹生、羅大愚、還有惜冰,再妻子朱紀, 地下工作羅總負責人輪流斧正,其間幾度增刪的信件,竟超過15萬字。 窮半生而得一著 《滾滾遼河》,林海音純文學出版社出版,小說長銷,締造了18年內48刷的紀錄,後達60刷 。中廣電台將其製作小說選播聯播;又由復興電台巡迴播放。1977年,中視更拍成12集的《遼河戀》電視劇在5月轟動熱播。 著作:散文《諸神退位》允晨文化1990、《做一個完整的人:群我文化觀》《原来如此》行政院文建會1995;早發表:《出埃及记》《虹霓》《火舌集》《葬故人》《愚狂曲》1《真相誰知》等。 滾滾遼河於1969年8月12日在中副連載後,引起了台日文學界的留神,日評家岡部昭彥更標明:這是不可讓人不知的革命事實…創價大學中國語文教授,在哈爾濱出生的山口和子即同步譯成日文。但譯著卻不如原著順當,被日封殺,直到1983年才得以完全面世,還被改編為舞台劇,於創價校慶以中文演出。 另有加藤豐隆,曾事偽滿,比較陽剛的日譯本在1978和1982出版,佳評如潮。在日引起讀者對這群可畏可敬的中國敵人,觸發中日民間的反省和迴響。 […]
羊圈中的小牧童
文:張薈茗 圖:鄭裕榮 寒風帶雪朔朔吹 薄衫的小孩仰起 紅通通的臉蛋 活像西部小牛仔 讓羊群在身邊穿梭 車奔於「獨褲」公路上,ㄧ陷一陡,如同蹦蹦車,始知塞外不堪行。沿途風沙滾滾,遼闊無邊,好像,走入無邊的太虛世界,陌生、驚悚;遠方的山谷,懸垂白色圓形氈房,矗立在山坳上,這是哈薩克祖先傳下的生活智慧,躲避狂風暴雪襲擊。 秦漢的騎兵彷彿自天山飛奔而過,陽關出塞已經不是做夢。眺望歷史天山,時而蒼茫,時而古木參天,白雪已經成群躲在山峰裡。 眼前,可愛的小牧童,跟著父母轉場,從小培養放牧基因,隨父母逐水草而居。秋天,美麗的季節,蘆葦變成黃金色的芒桿,白樺樹也被夕陽染成金黃,宛如走入黃金夢境。 轉場,是他們豐收的季節,滿山滿谷的羊群,在牧民跨馬揮鞭下,扭著肥滋滋的屁股,搖搖擺擺在公路上;這時,路上人車讓道,公路屬於牠們的勢力範圍,車速慢慢通過,欣賞壯觀的遷徙。可是,有些霸氣駕駛人,猛按喇叭,羊群驚慌四散,讓揮鞭牧民重新整隊,耗費精神。牛羊馬駱駝等牲畜,轉場在蜿蜒曲折風沙中。牧民說:「風雪來臨之前,必須趕幾百里路,回到適合人和牲畜過冬的暖窩。」 生於斯長於斯,小牧童很認命,他說:「羊是我的大玩偶,我從小沒有童伴。」 羊群已認得小主人,白天陪著曠野疾風呼嘯而去,夜晚星星月光照路相伴,牛羊就是他的玩伴。父母忙著轉場前的準備,他以小主人身份,忙著和羊群手足舞蹈,協助父母轉場,免得羊群失散,歷史上哈薩克人擅於騎射,曾造成中國塞外最大的夢魘,如征討,和親政策。
The 2018 GBCCA Annual Banquet
Dear GBCCA Members, The 2018 GBCCA Annual Banquet is to be held on Saturday February 10, 2018. It will be at Framingham Sheraton Hotel and from 5:30 pm to 11 […]